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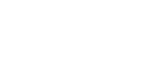
行 者 的 追 求
——访邹诗鹏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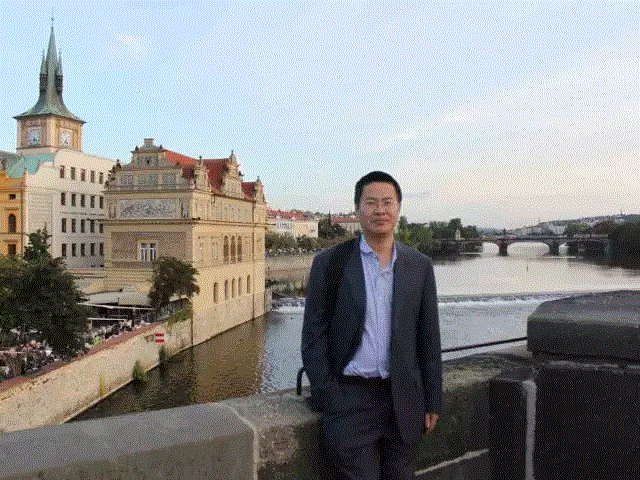
邹诗鹏,男,1966年生,湖北恩施人,湖北民族学院中医专业毕业后,在家乡一基层卫生院工作4年,1990年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先后获哲学硕士(1993)、博士学位(1999),导师均为张维久教授。1999-2001年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系国内首批哲学博士后,曾任教于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1993-1999)、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2000-2005),并任系主任等职。2002年2月任教授。2003年下半年赴美访学研究。2005年6月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
研究领域:生存论、唯物史观、社会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史、国外马克思主义及其激进左翼理论前沿、社会理论与现代性、当代精神文化分析、民族国家问题研究。近期主要兴趣:当代虚无主义、唯物史观与启蒙、古典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空间转向与激进社会理论研究前沿、中国道路与中国社会现实分析、中国多民族国家问题研究。著有:《实践—生存论》、《生存论研究》、《人学的生存论基础》、《全球化与存在论差异》、《激进政治的兴起》、《转化之路——生存论续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7、2008、2009)、RethinkingMarx(Washington,D.C,2007),Communicationacross Cultures: the Hermeneutics of Cultures and Religions in aGlobal Age(Washington,D.C,2008)。另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新华文摘》、《学术月刊》、等发表或转载重要论文150余篇。
采访时间:2016年9月14日
采访人: 刘茜(以下简称“刘”)
采访对象:邹诗鹏教授(以下简称“邹”)
结
缘
吉
大
邹:噢,“痛说家史”啊!这是我早年的经历,考入吉林大学硕士生以后,师生们还时常提起,刘福森老师还送我一个外号“小大夫”,在当时就传开了,很有趣。每个人进入哲学的方式都不一样,不同代际也不一样,一代人可能会有一种基于时代背景的相似性,常常也是一种谈资,但对后来者未必一定有太大意义,就当一种趣闻吧。我是在上一世纪80年代较为浓厚的启蒙思想氛围下对哲学发生兴趣的——我常常戏称自己是80年代“文化热”的“牺牲品”。我在大学读的是中医大专,高考体检以及录取时运气实在不佳,因此在大学时期即在想着如何改变命运,在大学期间以及大学毕业后,我的兴趣实际上已经从对中医理论的学习转移到了哲学的自学,并接触过不少哲学著作,从《自私的基因》、《存在与虚无》、《精神分析引论》到《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历史的观念》,其中大多没能读懂也不太可能读懂,但感到里面大有究头,连带着思考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跟我现在已经开始对中医展开哲学性质的自觉与体悟截然不同,当时是一门心思想从临床医学转为较为悠闲的专业哲学工作。但在当时,要从一介乡镇“小大夫”转为专业哲学研究工作者,谈何容易!只好硬着头皮考研,而且那个时候中国的大多数基层单位对考研并不支持(也较难想象能够成功考取),要费很多周折。我这个人,一旦定下目标,便会矢志不移地去做,其间确实吃了很多苦,经过了不少折腾与磨难,还报考过中医学史专业的研究生,但未遂。不过运气总还不错。1990年,在我被明确告知只有最后一年考研机会之时,终于考取了我所心仪的吉林大学哲学系硕士生。如果不是吉大,我无法设想此生该是什么样的生涯。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吉林大学哲学系的邹铁军教授(这位令人尊敬的先生现已去世,我是通过联系他报考吉林大学的)给当时还在山区工作的我发了一封电报,只有简单的四个字“已被录取”。可以想象我当时的激动心情!这四个字意味着梦想成真,意味着我居然可以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从事我梦寐以求的哲学研究了,安能不兴奋。如此兴奋劲,此前的人生中从未有过,此后的哲学职业生涯里,虽也有收获与喜悦,间有波澜和挫折,但与此经历相比,也多属平淡。就个人命运而言,毫无疑问,我有太多感谢,但理应把最重要的感激献给吉林大学哲学系,亦当努力有所回报!
这就是我当初的转行之路。我以为读哲学专业是很奢侈的,我自己十分珍惜。所以,在进入哲学专业之后,对于不少看低哲学或断言哲学不是一个好专业的观点,我从内心是完全不以为然的。在我看来,问题真得弄清楚:到底是哲学专业不好呢,还是我们这些从事哲学的人把哲学弄成了不好的专业呢?
刘:您在吉大求学期间师从张维久先生,曾有文章这样评价张维久教授,“著名哲学教授张维久先生”“……在治学与科研工作上,在哲学系与现代哲学所的创建上,均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在您的印象中张维久先生又是怎样的一位老师?您在老师身上学到的受用终生的是什么?
邹:吉林大学哲学学科名师辈出。我在那里读书期间,正是高清海先生后期那一段思想成果迭出、影响巨大的时期,在学问及其做人方面,毫无疑问我受到了高清海先生的影响。我并非高先生“正室”弟子,但在对我的培育及教化方面,先生对我用心甚多,也是得其亲炙,那时候我经常登门讨教,常常一连数个小时而不倦,至于博士论文,更是直接凝聚着他的心血,且得其嘉许,也是实实在在的导师,所以学界一些同仁也把我认作高先生的博士生。
上一世纪80-90年代,吉林大学哲学系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先生。高清海、舒炜光、邹化政、车文博、张维久先生均是国内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而孟宪忠、邴正、孙正聿、孙利天、姚大志、王天成、李景林、刘少杰、葛鲁嘉等的崛起,则令国内学界瞩目。1991年风华正茂的孙正聿老师回到哲学系执教,应是吉林大学哲学学科快速发展的一种标志。继高清海先生之后,孙正聿、孙利天、贺来等继续引领吉大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发展。
关于张维久先生,我很愿意多说几句。先生对我本就有知遇之恩。当年硕士生面试时,因我系外专业考入,当时决定录取时,导师组是存在一些顾虑的,是张维久先生定夺决定录取我并亲自带我,而我在工作几年之后再次师从他攻读博士,师生情笃。今天年轻一代的同学对这位老先生不是那么了解。张维久先生生于1933年,与高清海先生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二人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和同事,保持终生友谊。在人民大学期间,张先生读的是商品学,回到吉林大学以后因学科调整到哲学教研室,在刘丹岩先生的指导下工作和学习。他也是吉林大学哲学学科的开创者之一,创系过程十分艰难,张先生应是目前唯一健在的哲学系建系元老了。先生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他的著述及文章并不多,但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及其原著的素养,我近些年来做马克思主义理论史及其原著研究,同先生那时给我们打下的学养基础是很有关系的。张维久先生曾担任吉林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吉林省哲学学会会长。张维久先生为人宅心仁厚、开阔大气、公道正派,是一位高明的倾听者与对话者,更有很高的实践智慧,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情商甚高,在这些方面我自感也得到他的一些教益。张先生在学界拥有很大的影响,也有很好口碑及人缘。上一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相当一段时间,吉大马哲博士点以高清海先生为主,张维久先生为辅,但这个“辅位”十分的必要且重要。事实上,主要是通过他的努力,吉林大学马哲博士点才得以度过上一世纪90年代初的那一段艰难时期,很不容易。而在博士生培养方面,当时基本上也是高清海与张维久二位先生同时指导,张维久先生1992年评为博士生导师,是最后一批国务院评聘的博士生导师,而在此之前,他已经担负起博士生的实际的指导工作。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凡是高清海先生的博士生,同时也都是张维久先生的博士生,即使是在张维久先生自己带博士生的时候,这种合作模式也没有改变过,我们都是这一培养模式的受益者。如此培养模式,在现如今已经成为了美谈。现在张维久先生常居北京与长春两地,其身体硬朗,心胸豁达,思路清晰且仍健谈。是的,他仍然抽烟,显然受到师母的管束,弟子们会不时地去看他,分享师生情谊和快乐时光。宋代诗人陈潜心写有一诗,其中有云“福备宜高仁者寿”,适合送给敬爱的张维久先生。
刘:您是生存论研究方面的专家,在这个领域著述颇丰,影响也较大。能否为我们谈一下您有关生存论研究的缘起及其思路?
邹:这主要也要感谢吉林大学哲学系的研究基础及其创新传统。当时,在高清海、张维久、孙正聿等先生的指导过程中,同时也在同胡海波、田海平、贺来、徐长福、马天俊等学长、好友及其同学的闲聊及其交往砥砺过程中,我感到生存论转向问题值得研究,这也是关涉到当时实践观、主体性、人学、价值论以及文化哲学等等领域的深层次问题,而且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现代性问题的学理根源。此后的十年间,我一直在系统清理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并结合对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革命及其本体论变革的理解,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即实践生存论,实践生存论作为一项理论创新,既渗透到诸如主体性、人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以及实践哲学诸领域,还拓展到美学、文艺学、文化理论以及教育学等等学科,形成了较大的学术影响。2000年,我跟随张曙光先生在华中科技大学展开了较系统的生存哲学研究,这一研究在当时被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种创新尝试,算是这一时期涌现的人学、价值论、生存论研究范式之一种。我自己有关生存论的研究也仍在深化中,大约2003年左右,我开始从生存论阐释中国文化传统及其流变。在我看来,生存论与存在论,正是中西文化传统的存在论差别所在,面对西方语境中的生存论转向,东方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应当有足够的理论自觉,并积极地推进中华文化传统的现代阐释与转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现代转化的最积极的方面,也当从生存论维度进行阐释。
生存哲学或哲学生存论研究,是上一世纪世纪之交在中国形成的新的研究领域。事实上,正是随同国内一批志同者的艰辛探索与努力,生存论研究这一一度边缘且陌生的领域,终于成为国内哲学研究的“显学”。这的确要感谢一些哲学前辈特别是高清海先生的大力支持,也要感谢同仁群体的相互激励;而若干批评,也对深化和开放本领域的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
刘:听老师们讲,您总是追求学术理论的开拓与创新,且总是能够站在学术研究前沿。从简介中能够看到,您目前正在从事多个领域的研究,看上去铺得很开,你从吉林大学毕业之后,去过武汉,然后又去了复旦大学,能否就这些年您所取得的成就作一个介绍。
邹:我愿意做一位行者,多为劳绩,不愿谈所谓“成就”。
我1999年离开长春去武汉,先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做博士后研究,后调往华中科技大学。在开展哲学生存论研究的同时,也协助欧阳康与张曙光二位先生创办一个专业哲学系,后担任系主任等职。在2005年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系2006年升格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之后,我的研究又发生一定的变化,具体地说是从生存论研究向更宽的论域拓展与深化,这一变化是内在的,而不是形式的转变,而且也算是在吉大期间形成的一些问题意识以及学术论域的延续和拓展。
我有自己的学术判断。总的说来,当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大有可为,大体说来,在西方当代人文社科学术多已满足于现代性及其理性化沉淀下的规范模式时,当代中国则因其复杂的内、外部境遇及其现代文明建构任务,哲学理论研究更为多样、滞重而艰巨,也给中国的哲学理论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个人则努力追求以学术理论的方式呈现现时代的深度、丰富性及其历史自觉,激发理论想象,推进学术理论的创新与创造,反躬内省,拒绝自满,追求超越与自我超越,格局要够,研究要实。大约十五年前,我即很不愿意陷入某种已经模式化的生存论话语系统中,而是致力于相应的拓展与深化,其中现代性问题研究的特征特别自觉,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抓手。你看到我目前的研究领域有些宽,但其实都是有序的。具体而言,我目前的研究主要在如下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个方面是深化哲学生存论研究,开展虚无主义的专题研究。2013年出版专著《转化之路——生存论续探》,此著揭示现代生存论何以不同于存在(BEING)传统之生成(BECOMING)传统及其渊源,揭示生存论何以构成唯物史观的理论环节,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之间的内在关联。虚无主义则是生存论在实践及实际层面的拓展,是我这些年投入较大的研究领域,目前国内一批同仁也在致力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近些年我在这方向发表了一些论文,引起了不少关注,今年即将出版一部虚无主义研究的专著,敬请方家批评。第二个方面是展开思想史理论史以及社会政治哲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这一方面,已出版《激进政治的兴起————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政治与法哲学批判手稿的当代解读》,并即将出版专著《从启蒙到唯物史观》,前后发表了一批重要论文,并主编《思想史视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目前已经出版6部著作,有《青年马克思与启蒙》、《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重释人的解放》等。国内一批同仁也在致力于本方向的研究,比如张盾先生就很具有代表性。目前,社会政治哲学及其思想史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也是我所在的复旦大学马哲学科发展的重点方向。在这一方向上,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内一批青年学人正在成长起来。第三个方面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及其激进理论前沿方面的研究。到复旦大学之后,我及一批同仁承担了学科重大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年度报告》,研究过程中我们对国外有关前沿有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把握,并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研判,最近几年来我致力于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及其激进左翼理论前沿的若干主题,如新帝国主义、空间转向、身体理论、生命政治学的兴起、斯宾诺莎复兴等主题,如此前沿性的研究,对于提升基础理论及其现实问题的研究总是有益的。第四个方面是展开中国道路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学人而言,都有必要以自己的方式研究中国问题。我探索的问题主要包括:中国道路的文明性质;中国道路与中国实践哲学;中国道路与世界历史逻辑的重建;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状况分析;中国精神的历史形成及其现实呈现;当下中国社会建设与制度文明建设。目前特别致力于探讨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重建问题,这里面值得探讨的问题甚多,还需要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与哲学性质的探讨,也就越做越有意思,当然也的确感觉到精力有些顾不过来。
刘:听上去您现在的学术面铺得确实够宽的,研究的强度也蛮大,你对以后的学术生涯还有什么考量?另外,我们注意到,您曾先后在多个时期同时担任行政、教学与科研的领导工作,你是如何兼顾和协调的呢?因为目前在很多高校教研、科研和行政的“三重任务”似乎成为了部分高校青年教师们职业发展上的“拦路虎”,而苦于无力协调?你能否在此方面给青年教师们一些建议?
邹:是啊,我与同事孙向晨院长开玩笑,说我一直在打洞,打游击。向晨回说:没事,等打到一定程度就通了。这话当然有理,但打不打得通还得看火候,还有就是运气。目前还得打洞,而且尽可能打深一些,让后来人继续做的时候有一定的基础,而不是狼藉一片,因此还须用力用功且要得法,不过已经有一些豁然之感了,因此就总有一些欣悦感。因为要全力以赴,所以就要尽量少做无谓的折腾,我致力于做尽可能大气开阔的学术,但尽量选择小众的生活,也尽量少迎合时语,学术生命总是有限的。当然,在诸多方面,其实还是可以培养后来者来做的,我在研究生培养上就特别上心,碰到好的苗子,培养个十年八年,总可以做出不错的学问来。
至于行政、教学与科研三重任务的协调经验,我的确钦佩那些能够很好协调这三者关系、且学术做得像模像样的学者,他们不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付出了特别的辛劳,但我自己却没有这种能力。在我的经历中,实际上是尽可能避免陷入科层化且越来越繁杂的学科建设与管理事务,除早年在基层医院做过一些行政管理工作外,在我的学术职业生涯中只有五年左右的时间在兼做院系管理工作,其它时间大都集中于科研与教学主业。现在所兼做的一点协调组织工作,主要而言是学科性质的,谈不上分心,复旦的学术传统还是比较注意保护学者的专业志趣的。
从早年一介中医转入哲学门,迄今已有26年,诸多艰辛与劳绩,系于感念。对于前路,我仍然选择力行,行者应无疆,这一时代的哲学恐怕也有必要超越其看上去确定无疑的大学及其学院化视域。与此同时,一个人恐怕还应当做所在年龄应该做的事情,年过五十,自然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理,无为亦为行。面对学术传承,更当选择清醒与谦卑:后来者必定会走得更远!
